有没有一个价值让我们安定下来
时间:2021-03-15 来源: 作者: 浏览次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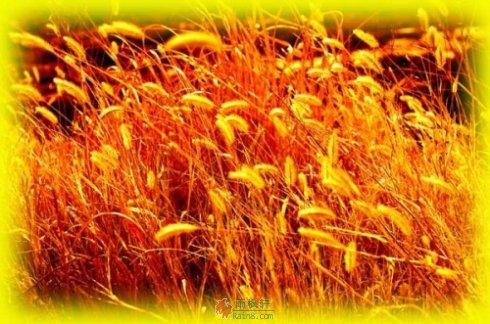
这两天微信朋友圈被一篇清华毕业生因为买不起学区房而离开北京的文章刷屏。一开始我以为是投诉帖。在任何时代,都有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没想到这个话题在全民中引起了一波焦虑和恐慌。我们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西西弗斯,一辈子都是荒谬而徒劳的。
知识能改变命运吗?努力学习,努力赚钱的目的是什么?观念的碰撞反映了不同阶级、不同时代的价值取向。我们大多数人都只是普通人,越来越难以克服或逃离原来的阶级。人们普遍感到困惑和失落。他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该做什么。他们被时代的巨变困住,抓不到救命的稻草。
每个周五去复旦上辅导员课的路上,都会路过四号线一个很神奇的风景:附近一栋低矮破旧的老房子,稍远一点的高层商品房,最远的是东方明珠、世界金融中心、上海中心。今天看着窗外的风景心想,我买了学区房去复旦,但是去了复旦就买不到学区房了。如果附近破房子拆了,我可以直接投资美澳的学区(没错,你看过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乌托邦,学区是全球性问题)。那你为什么没有绝望地死去?作为一个读过书的年轻人,一个正在教书的年轻人,一个相信知识的年轻人,我的内心也是汹涌而迷茫的。
我的祖父母出生在一所学校,一生都在一个小镇上当老师。爷爷奶奶有知识,但很少过问孩子的成长,奶奶则希望孩子的教育水平永远保持在足以教中小学的水平。小时候我觉得她很高兴我能读诗能背诗,很害怕谈文学作品里的思想感情。初入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在饭桌上和爷爷聊起课文里的鲁迅,奶奶却用筷子敲着碗叫它停下来,尽管隔墙有耳,大家都有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长大后,外婆希望我们家每个人都能安居乐业,永远不要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理解她为什么总是坚持让我大学毕业后就停止学习,总是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要求我和妹妹去教书。现在,我明白了,把所有人都推上同一条轨道的简单粗暴的背后,是深深的恐惧和警惕。对于爷爷奶奶来说,知识是一种家庭信仰,但“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却成了家庭灾难,令人可怜和悲哀。那些出生在读书家庭,教人受教育的人,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因为读过书而突然成为罪人,会坐牢认错;我不认为有一天我的孩子会因为读过书而不再有学习的机会。
大舅和二舅在农村插队度过了青春。后来我舅舅因为喜欢拉二胡,差点成了无锡锡剧团的演员。后来他自学英语,在一个小镇教英语。他是个傻瓜和愤世嫉俗者。他很聪明,但他从来没有用心做过任何事。我觉得这和他青春迟来有很大关系。我叔叔成了工人,娶了个农村老婆。我妈妈是最小的。她中考以优异成绩考入县城,但因家庭成分较差而无法就读南京邮电学校。她在家乡的师范学校上学。我妈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上大学。记得我毕业那年恰逢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校庆,学院给了我们每人一件绣有校徽的学位袍。我妈妈非常喜欢那件衣服。她在家里戴着它,让我爸爸给她拍照。
在我的记忆里,我爷爷晚年总是偷偷买书收藏,读书谈书的时候也是如痴如醉。他很高兴我在读中文系。爷爷去世后,奶奶住在一套旧公寓里。在老年公寓里,因为她读过书,会画中国画,会弹风琴,她是一个不同的老太太。有一次电视台去采访她,她很开心。
从爷爷奶奶那里,我了解了传统学者的信仰。读书不是为了改变。如果非要给读书一个世俗的意义,反而可能给你带来痛苦:在古代,科举失败是耻辱;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恶的。那么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呢?读书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人”,一个站立的、大写的、丰满的人,一个自由的人。知识是一种力量,只有把求知作为一种根植于心的信念,才能不被时代的洪流冲昏头脑。
我的祖父母是文盲农民。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苍白最普通的人。他们的前辈,他们的前辈,就像地里的庄稼,默默的,野蛮的生长着。
小时候真的不喜欢回爷爷奶奶家,不是因为条件差,而是农村生活让我觉得单调、无知、无聊。我无法想象父亲是怎么从这样一个不爱读书的环境考上大学的,但他也很佩服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应该不知道什么是读书,但我相信他们相信“读书改变命运”,否则他们不会在一个吃不上饭的年代,尽最大努力给我爸提供读书。父亲很幸运。他是长子。他世上有两个姐姐,世上有两个弟弟。他们俩都没读过书。在这样的家庭里,读过书的人都会受到尊重。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喜欢叫爸爸。
和爷爷奶奶在一起,我明白农民的信仰。他们处于社会底层,只相信能改变命运的东西。古代有农民起义。在父亲的日子里,我点着煤油灯去参加高考补习班。在这个时代,我不知道。可能是去上海的硬座票吧。
爸爸参加了
三次高考,于1980年考入苏州大学。他最喜欢跟我讲的一个日常生活场景是,那时候佩戴苏大的校徽乘坐公交车,一定会有人让座。如今每当看到媒体报道农民工怕弄脏座椅而宁愿蹲在地铁里,我都会想起这件事。
知乎网上有人说,那个年代的大学生能成为社会精英不是因为考上大学,不是因为“知识改变命运”,而是因为他们大学毕业包分配,他们在青年时期就掌握了中国社会的权力和资源。我不否认这句话部分正确。可是首先,包分配对当年的青年们来说,不能选择,如掷骰子般没人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里。据说爸爸班上有一对互相爱慕的青年学生被故意拆散,一个被分到江苏的最南边,一个被分到江苏的最北边,过了好些年才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像我爸这样的农家子弟,则被毫不犹豫地扔去了苏北。其次,人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你的起点,人生的意义更无法用金钱与地位去衡量。这么多年过去了,爸爸的同学有的早已离开原来分配的岗位和城市,有的下海创业满世界飞,有的位高权重,却因为过得不快乐而选择结束生命。我们为什么要把那一代人的人生路归因于年轻时一个无法选择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