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书
时间:2021-04-23 来源: 作者: 浏览次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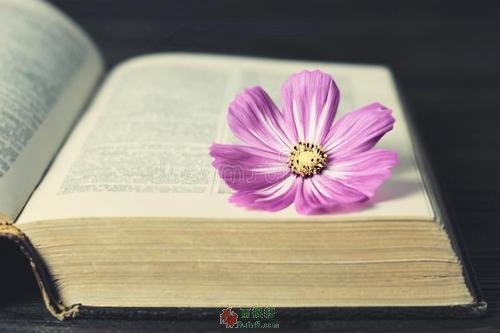
从小到大,我学了这么多年,然后教书。我每天过着没有书的生活,处理的书最多,读的书也很多,但是我读不完妈妈的书。
忙碌了一天做饭、洗衣服、喂猪、鸡和鸭后,我妈妈会叫我:“小春,去拿我妈妈的书。”
我会问:“哪本书?”
“那个橡皮纸的。”
我知道我妈妈今晚很开心。她想陪我在书房里,用植物油灯给爸爸绣拖鞋。
橡皮纸的书里没有一个字,真的是“无字天书”。书中有红色、绿色、彩色的丝线和用白纸剪成的图案。还有一双奶奶给我妈绣的水绿色缎子鞋面,还没做成鞋,我妈就这样被书夹了快十年了。奶奶早就去世了,绣在水绿色缎子上的樱桃依然鲜红得可以摘下来吃;一对小喜鹊,一只张着嘴,一只闭着嘴。我妈跟我说,张着嘴的是男的,闭着嘴的是女的。每次我妈妈打开一本书,她总是翻到最厚的一页。看着一对喜鹊看了老半天,嘴角似笑非笑,眼睛呆住了,像是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又像是在思考着什么。然后翻到另一页,仔细挑选丝线,绣上花朵。鞋面上的喜鹊和樱桃似乎是母亲永久的样本,她心中的图案和颜色似乎也随之改变。
为什么妈妈把这本书叫做胶皮书?是因为书页又厚又硬,像树皮的颜色,而且是用一些材料做的。它们很坚韧,翻过来也不会被撕破,还能防潮。妈妈给它起了个新名字,——胶纸。其实这是一张很旧的纸,是我奶奶剪下点的,传给我妈的。书页是双层折叠的,有时候妈妈心里的宝夹在中间,就是爸爸的北平来信,才是“无字天书”里真正的“书”。在我面前,我妈从来不拿出来重读,直到花儿绣腻了,植物油鼻烟淡了。我背着《论语》 《孟子》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然后她悄悄拿出信,隔着钱山跟她爸爸小声说了自己的自信。
母亲离不开的另一本书是帝王历。她在床的抽屉里和厨柜的抽屉里放了一本,随时拿出来搜看是哪天。生命对母亲来说太重要了。她什么都小心翼翼,什么都想走运。买小猪,修笔,插秧,割米,更别说腊月酒蒸饼了。只有母鸡孵出了一窝小鸡,她不能选择哪一天,但她也想看看帝历。如果她遇到了顺境的好日子,她会很开心,以为这窝鸡会顺利长大;如果刚好是糟糕的一天,她会告诉我要格外小心走路,不要踩到鸡,小心被院子里的老鹰抓走。有一次,一只鹰俯冲下来,她妈妈放下锅铲跑出去抓鹰,却把一只鸡叼走了。妈妈跑得太快了,不小心踩到了一只鸡,折断了它的小翅膀。鸡哭得很惨,母鸡在我们身边呜咽。我妈一歪,差点摔倒。我帮她坐在长凳上。她把受伤的鸡捧在手里,后悔踩了它,为被鹰叼走的鸡伤心。眼泪不停的流,我快要哭了。
日历年二十四节气,我妈都背熟了。每次打开御历,我都想弄清楚这个节气在我面前的是哪一天。她总是从头读到那个月的节气。我也背诵:“立春,下雨,蛰人,春分,清明,谷雨……”但每次读到千年,秋分,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有一种悲凉的感觉。小小年纪,“一年易秋风”之感油然而生。也许是因为八月有个中秋节,诗里有那么多描写月亮的句子。中秋节应该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年年盼望着。我父亲和大哥在北平总是迟到。还有一个老师教我《诗经蒹葭》:“白露是霜。所谓的伊拉克人都在水侧。从它回来,路漫漫其修远兮。来回奔波,是在水中央。”当时我还不太懂《万在水中间》,觉得有点好笑。前两句是我最喜欢的。“白露是霜”让我想起了“鬓角霜”,老师教我的是对白发的比喻。我经常抬头看妈妈的额角,看有没有“鬓角”。
《本草纲目》是一本给我妈妈学的书。木字旁边和草字开头的字太多了,我妈真认不出来。但她总是把它端端正正地放在床头柜上,偶尔翻一会儿,也是轮廓分明。其实是我爷爷山乡阆中口头给她的,我妈只知道仪式在这本书里。
我妈从来没有正式认过字,也没有读过书,但在我心里,她消息很灵通。
本文来自华纳娱乐文学网 转载请注明
上一篇
下一篇